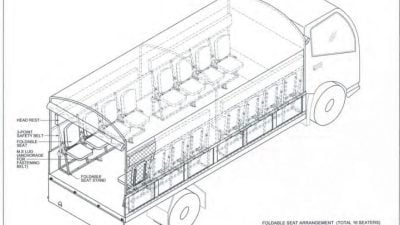记者心视线 | 吕紫莹:烟霾背后的我们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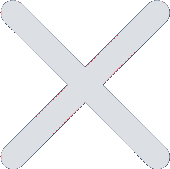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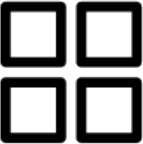
“蓝色向外面,白色向里面,铁丝压紧鼻子。”
戴口罩的“技能”是我爸爸教我的,第一次戴它不是因为疫情,而是烟霾。这句话伴随着我成长,更是成为季节标志。每当天空泛灰,空气散发烟味,它就会在我耳边响起。
ADVERTISEMENT
小时候我不明白什么是烟霾,只觉得自己能和医生一样戴着口罩。可是,口罩让我鼻子发痒、呼吸不顺、说话声音很闷……酷感变成烦躁。可口罩摘下,鼻子变得更难受,因为我是个鼻敏感的人。
那时,我坐在靠窗的位置,远处就是一座山。它不再鲜亮,沉闷的灰色取代了它,教室也被笼罩,每个人的声音都模糊不清,而这个颜色不该属于童年。
长大后,我才知道这不是天灾,而是一场不断重演的人祸。
如今,我是一名实习记者,日常早上9时开车出门。车窗外的天空总是灰的,它不是阴天的灰,而是一种说不清的“脏”。它像一张透明的磨砂纸被揉皱后,覆盖在我们的周围。
这么多年过去了,我的鼻子依旧不舒服,只是这次不再有爸爸提醒我要戴口罩,而我也不觉得戴口罩是个特别酷的事情了。
最近,空气的味道又变了,散发出一种燃烧过的灰烬味。
回到办公室,我听到大家在讨论空气素质、API指数、哪里可以拍到“烟霾感强”的照片。甚至,我的朋友们也互相比较谁在的区域API指数更高。
我常想,我们是不是无形中把烟霾当成“习惯”,和路上塞车、涨价、政治冷感一样。以至于每个人都知道空气出了问题,但没人觉得这个情况需要被改变。
这些天,我的日常围绕着打喷嚏、喉咙干疼、拼命喝水,总感觉自己快和烟霾融为一体。平时在草场晨跑的邻居也不见了,偶尔看到有些人戴着口罩,只有路上的车不变。
小时候,我常听大人说“今年比较严重”,以为以后会更好。事实上,我们有应对的方式,但它们只是让我们适应糟糕的空气。
“反正每年都会有,就忍一忍吧”的习惯正慢慢削弱了我们追问背后责任的力气。
我们无法阻止一场野火的燃烧,更不能立刻改变整个农业系统的焚烧方式。可是,我们连“表达不满”的声音都放下,只剩下习惯与顺从,那些本可以改变的事情,就真的被当成理所当然了。
我们曾经以为成长会带来更自由的选择,可如今我们甚至连“想自由呼吸”的资格都要靠天气决定。
我们可以选择不谈政治,不追热点,不加入争议,但我们无法不呼吸。
很多人都在咳嗽、打喷嚏、鼻塞、头痛。大家都在经历一场无声的环境灾难,但我们似乎习惯了,这就是“生活的一部分”。
我想起,小时候坐在教室里,那扇窗外的山朦胧,我曾以为是天气的错。现在,我知道不是天气,不是自然,而是人造。
那年,我以为戴上口罩很酷,现在我只觉得闷得喘不过气。烟霾袭来,我们从学生到长大了,始终逃不开这片灰。
ADVERTISEMENT
热门新闻





百格视频





ADVERTISEMENT